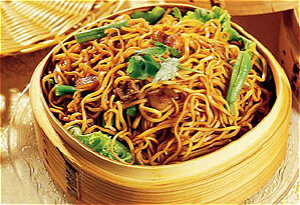对于面,北方人多是有着执念的。一副即使听了再多道理,不吃一碗面也是过不好这一生的情肠。事实上,面并不仅是北方人的专利,牛肉面则更非如此。被称为我国四大牛肉面的,除了家喻户晓的兰州牛肉面,还有来自台湾的川味牛肉面,四川的内江牛肉面与湖北的襄阳牛肉面。这一看不打紧,原来四者竟有其三都是来自南方,这让嗜面如命的北方人情何以堪。

巨大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侵入血液的南北差异。正如许嵩《断桥残雪》中那句“江南夜色下的小桥屋檐,读不懂塞北的荒野。”民国著名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曾言:“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这便从地理角度给南北方人的“质”做了诠释。质所不同,文风必有异,其实于饮食亦然。根植于不同地域文化的牛肉面自当各有其特色。

台湾牛肉面,现已成为台湾著名美食之一,台北市更被称为“牛肉面之都”,每年都要举办历时三个多月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马英九也在多个场合表示欢迎各地造访者来台湾尝尝地道的牛肉面,大有搞起“牛肉面外交”的派头。经过多年的沿革创新,台湾牛肉面现已发展出红烧、清炖、葱烧、沙茶、番茄、咖喱等多种口味,其中,仍以经典的川味牛肉面为冠。川味牛肉面是1949年前后由随国民党军队到达台湾的四川老兵所创,筋道的手擀面配上半筋半肉的黄牛肉,浇上肉骨红汤,口感醇厚而鲜辣。捧着一碗面,捧起的是家乡的味道,填补的是无法言说的流离之痛。台湾牛肉面,吃的是乡愁。

内江牛肉面,素有“巴蜀小吃之首”的美誉。根植于巴蜀的牛肉面,特有一番精致与讲究。面条细薄而碱味浓,被称为“水叶子面”,口感细腻。牛肉则优选贴近肋骨,带筋或带肥肉之肉块,先经大火烹炒,再加豆瓣酱、姜、蒜、八角等多种佐料小火长炖,直至牛肉入口即化。汤中所用辣椒油是用四川特有的被称为“糍粑海椒”的做法制成,这样制作完成的辣椒油辣中自带淡淡的糊香。此外,汤中更多加韭黄调味,别具风味。总之,内江牛肉面,品的是细腻。

襄阳牛肉面始创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一直是襄阳群众最喜欢的早餐。它讲究麻辣鲜香,尤其崇尚回味悠长。略透碱香的襄阳牛肉面其实并不都加牛肉,多是加一勺牛杂,用秘制香料烧制,细嫩而不肥腻。面汤所用的中药卤包一直是最为神秘的所在:牛油、大骨、辣椒,配上多种香辛料,小火煨制6小时,看上去红油油的一锅汤,吃起来却不辣口,不上火。此外,襄阳人吃牛肉面多配上乳白色的未加大曲的襄阳黄酒,初见这搭配略显怪异,日久方知非如此吃法不足显襄阳之意味。
襄阳地处汉江平原腹地,汉水穿城而过,是历史上的“华夏第一城池”,连接着华夏文明的楚文化、汉文化与三国文化皆发源于此。当年刘皇叔三顾茅庐造访孔明,二人促膝抵足谈尽天下大势,千古流传的卧龙“隆中对”的故事便发生在襄阳。襄阳更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商业要地,无数的战役、成败、英雄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流中。襄阳的美好,在于汇聚着古中国的智慧,在于碰撞着数不胜数的传奇。在这样厚重的历史中,襄阳牛肉面怎能缺了回味的悠长?又怎能缺了那碗醉人的黄酒?其间惬意,怕不足为外人道也。在这热气腾腾的红汤与白汤中,襄阳牛肉面,发酵的是历史。
在兰州,正宗的牛肉面讲究的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黄亮的面条,满满浇上熬到清透的牛骨汤,配几片爽口的白萝卜,再加上一小撮香菜以提味,最后根据个人口味泼上红油辣子,真是满足到过瘾。

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对牛肉面的称呼可谓多矣,叫“牛肉面”都已经算是文艺,更多人亲切地称它“牛大碗”,抑或简称“牛大”。这一声“牛大”,便含了多少西北人特有的豪爽与大气,更含了多少对牛肉面特有的热爱与不见外,即使我这个外省人恐怕也能感受得到。
远在西北内陆的兰州牛肉面,偏偏可以享誉全国,本身已是一奇。内陆的封闭带来地处内陆城市的保守,殊不知,兰州却独独是个例外。上天不仅不许兰州封闭,反而许给它无限可能。

兰州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碰撞着人类历史上最具代表的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文化不断地碰撞与融合中,成就了今日兰州的胸襟。而自西向东穿城而过的黄河更为本应封闭的兰州扯开了一条口子,便利的水陆交通为兰州带来了走出去的可能,使其成为连接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桥梁和纽带。
特殊的地理环境同样带来了特殊的食材。兰州南面的甘南草原环境纯净,盛产的牦牛肉肉质纯粹,肥瘦适中而带清香,实乃肉中上品。河西走廊干燥少雨的气候培育出的小麦,尤其具有劲道的口感。当丰富的牦牛肉一朝遇到充足的谷物,如同一场期待已久的化学反应,通过回汉拉面师傅的技艺发酵,兰州牛肉面绽放出热烈奔放而又旷日持久的魅力,闪现着兰州人饮食上的智慧之光。

然,一碗牛肉面,生于南北则不同,而离开了本土的兰州牛肉面,又必有着几许尴尬。常听有人抱怨,兰州牛肉面根本不好吃。来自面霸之乡的兰州人自然不服,并一语道破天机,“牛肉面离开兰州就不对味!”大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叹。
兰州人之叹未尝无理。兰州本地面馆的招牌从不自称“兰州牛肉面”,更无“兰州拉面”一谓,而遍布全国的“兰州牛肉拉面”则大抵为外省商人冒名伪称,盖失了“牛大”本味,怎不让人气恼。而一旦出了兰州,牛肉面的食材也更为难觅。姑且不谈兰州特有的小麦与牦牛肉,就是牛肉面所必需的辣子也难以重复兰州的味道。西北的辣子是最让走南闯北在外的兰州人记忆深刻的。油泼辣子则是将上好的辣椒面淋上热油,那冲天的香气,不禁让人食指大动。而离开了兰州的牛肉面,失去了这些特有的原料,便先天不足了。曾有到南方开面馆的兰州师傅,坦言当时苦于找不到和兰州口味相当的牛肉,便不辞辛苦专门从兰州运牛肉过去,才做出与家乡口味接近的牛肉面,然也仅是接近而已。

除了面,牛大最为精髓的部分莫过于它的汤。所谓是否入味,能否让人念念不忘而终于去而复返,全看汤的功夫。汤的熬制最为讲究,兰州人多喜吃第一锅面,为的就是吃到早上新熬的骨汤浇的头锅面,汤最清也最鲜。兰州的海拔在1500米,水的沸点是95度,在这个温度下熬制的骨汤才成就了兰州牛肉面特有的味道。离开了兰州特殊的地理环境,牛肉面变了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说,兰州牛肉面品牌杂乱,店面规模也小,就餐环境更是一般。这不懂扩大规模的土法经营和土的掉渣儿的甚至让顾客露天站着吃面的服务意识,真真与现代化都市化的趋势格格不入。殊不知,这一贬之间,却又道出了牛大的另一份真趣。
与《红楼梦》里工序浩繁,要用十几只鸡来配的茄鲞等供显贵阶层品用的食物不同,牛大本是物美价廉的日常食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寻常百姓,在一碗牛大面前却实现了彻底的平等。当他们在大大小小的面馆或站或蹲,此起彼伏吸溜着眼前这碗牛大,嬉笑怒骂间一起感受着味蕾刺激带来的终极满足时,便都是些地地道道的西北人,何来他别。人生本不就如此吗?追名逐利,阅尽繁华,最终却返璞归真到一碗牛大。

来一碗牛大,吃的是正宗,是包容,更是这份真趣。
多少人人到中年,行遍南北,历尽炎凉,却愈发能在南北各异的牛肉面里尝到人生百味,顿生感慨。用一碗牛肉面去代表一片土地、一段历史,自然是有失偏颇的,然而,牛肉面却永远无声地讲述着那一方人,那一方水土。这也许就是尝尽大江南北牛肉面,所该品到的食中之味了吧。